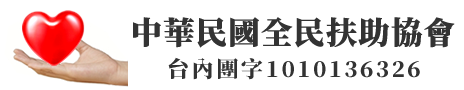- 首頁
- 協會快報總覽
卡奴悲歌..過度消費並非故事的唯一
50萬卡奴悲歌-並非過度消費2000年開始,台灣經濟逐年衰退,企業大型化,壓縮了中小企業,後來台商西進中國,失業的人口逐年攀升。街頭遊民的面孔越來越年輕,媒體開始小篇幅的探討是不是失業人口年齡層往下降,導致街頭開始出現年輕遊民?但是頂多一二個社工或萬華商家的說法,從來沒有失業的遊民出來現身說法…… 萬華跟台北車站一直是街友群聚的大本營,但是當時我還是很嫩的記者,那個凌亂的環境跟人群,還是令我卻步。訪問藝人張琪鬆動了我對街友的印象,張琪有個特別的經歷是她接觸輔導過遊民,他談到從2000年到2006年,街友淪落街頭的原因有哪些變化?比如2000年開始,失業潮非常嚴重,很多人失業不敢跟家人講,每天早上還是照樣提著公事包出門上班,其實是在公園,一待就是整天。 **失業之後 我與家人面目全非**變成遊民是逐步來的。失業後,覺得自己沒工作很沒面子,開始放逐自己、不認同自己,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。他覺得反正自己也不是一個人物了,逐漸也不在意外表、談吐和清潔了。以前每個月拿薪水回去養家,後來連家也不回了。當人不敢面對現實、一直找理由逃避,到後來連人生的方向感也沒有了。 我們總以為遊民就是墮落才愛喝酒,但是有時喝酒是為了保暖,或者逃避痛苦。張琪說她當時經常跑台北縣,就是現在的新北市,每次到了冬天,常常早上就會看到遊民死在公園。因為很冷,這些遊民又喝劣質酒,喝酒的時候,體內很熱,可是夜裡,外面溫度才7、8度,造成心臟麻痺;而且,喝完酒會散熱,有時失溫就凍死了。遊民在外遊蕩久了,本能會退化,長年在街頭餐風露宿,精神身體都容易生病。 隨著失業人口的增加,卡奴也增加了,張琪說,後來竟然也有卡奴淪落街頭。張琪甚至曾驚見一家子帶了小的在街頭躲債,父母因為怕孩子受到討債公司的威脅,不敢讓小孩上學。當時許多銀行將債務委託給討債公司去索討。 張琪在人安基金會幫忙,就看著遊民不斷增加。她說,像基金會2000年以前,幫遊民辦尾牙才50張桌,到了2006年已增加到320桌,尾牙當天早上不到8點半就有人來排隊搶位子,只因這頓飯做得比較豐盛,這些人已經盼了1整年。 主流媒體喜歡包裝新聞,少有社會這麼陰暗面的報導,回到我們的成長經歷或從小讀的課本裡面,也從來不會跟我們講社會這麼真實的一面,就像台灣這麼多人離婚,外遇跟劈腿,少有媒體很嚴肅地去談過這些事。還有,明明底層人佔社會人口很大一部分,可是媒體有好好了解他們嗎?這些底層人物到底經歷了什麼事?難道把問題歸因於就是這些人不夠努力,我們就滿足這個答案嗎?的確,台灣不少人都是這樣看這群人,把一個人的失敗導向於個人因素,可能很多社會也是這樣,可是當你這樣看問題的時候,你就會忽略社會結構是如何不利於這群人。 多年訪問,看到很多人因為失業,再加上意外,就很容易像溜滑梯一樣往社會下層跌落。2006-2007年,台灣社會發生嚴重的卡債問題,造成非常多的卡奴,很多卡奴被銀行逼債,有人跑路,有人自殺,很多家庭的日子根本過不下去。當時律師林永頌帶著一群律師幫忙這些卡奴,跟銀行法院協商債務。當時我就訪問了林律師。 大家都認為,欠錢還錢,天經地義,還有什麼好說的?林律師原本也是這樣認為,甚至以為這些卡奴都是因為買奢侈品,但是他在了解卡奴後,才發現有人失業,跑去開計程車,但是SARS期間沒有客人,接著老婆生小孩又早產,只好跟銀行借錢。他來找林律師幫忙的時候,已經連續開車開了32小時都沒有休息。他拚命開計程車還錢,但是怎麼樣還,都還不到本金,因為當年銀行循環利率高達20%,而且是複利,借80萬,兩年就變成好幾百萬,結果錢愈還愈多。林律師曾經開玩笑的問他:「為什麼不跑掉算了?」結果這計程車車司機回他:「我跑掉,以後是要怎麼教育我的小孩?」他是個老實人,想還錢,也真的一直在還,如果不是利息這麼高,他早還清了。林律師說,像他這樣的司機,他至少認識幾十個。這個司機也曾經想過要自殺。 *五十萬卡奴悲歌 並非過度消費*我有個記者朋友夏傳位在他寫的《塑膠鴉片》一書裡提到,2000年開始,台灣的信用卡跟現金卡雙卡借貸急速上升,卡奴形成的這段時間,正是台灣經濟衰退,失業率飆升的時候。根據他的調查,五十萬卡奴裡,其實過度消費的只佔12%,而失業卻佔了將近六成。所以,過度消費並不是卡債高築的主要原因,失業或人生的重大變故,還有離婚才是。我後來訪問夏傳位,針對卡奴過度消費這個問題,他覺得,就算是過度消費也沒什麼好譴責的,因為現在社會,消費已經是經濟成長的驅動力,政府、廣告跟媒體每天都在鼓勵大家消費,個人現在也是透過消費自我定義,大家多多少少都會去吃大餐、買手機或者名牌奢侈品,過度消費已經是現代社會的高風險,只是有些人在變成問題之前就處理掉了,卡奴只是因為處理不好往下掉而已。夏傳位採訪很多案例,很多卡奴起先都是消費,後來真正出現大筆費用,都是因為他開始失業或家裡出狀況,他去預借現金急用。 沒有遇過這種事的中上階層跟高收入的上班族,每個月都有盈利或固定薪水進帳,無法體會突然斷了糧,或是看到存款不斷探底,那種焦慮與心慌。可是一般家庭,很多都沒有存款,當因為失業沒有了收入,即使全家不吃不喝,都要付房貸、生活費或孩子的學費,最後就只能跟銀行借錢。有人認為卡奴,街友,都是極端現象、罕見案例,可是如果你去問問身邊人,恐怕並非如此。我曾訪過一個在就服站,幫失業朋友找工作的二度就業婦女,就是所謂的就業媽媽,當她很有成就感的跟我談完,她如何成功幫忙兩個失婚婦女找到賣手搖杯的工作後,突然跟我說,她其實是負債上百萬的卡奴,因為在做這工作前,她也曾失業多年,就靠借錢付小孩學費,過日子。後來她在就業服務站找到的工作也不穩定,因為那是政府外包給廠商的工作,一年一聘,還要看業績,才可能續聘,而且薪水也不高,她無法償還卡債的本金,每月就只能繳交最低金額,而龐大的利息還持續在滾動著,她無能處理,只好暫時擺著。我真的很意外,一個幫人就業的人,竟然自己也曾經長年失業,而且自己的工作也不穩定,隨時怕被裁員,還背負著百萬卡債。 我常遇到一種狀況,你原本帶著某個問題去採訪某個人,可是你發現了他另外一個驚人的故事,這些故事很難想像的發生在他身上。 其實採訪這些人,我有個觀察,台灣社會的救助體系還是不夠完善,大多數人靠的還是家人、朋友的支持。像我每次採訪這些街友往下墜落的過程,我就常常覺得我跟他們只是一線之隔。我自己也遇過不如意的事,我曾經難產,接著孩子早產,有幾年時間非常失意辛苦,可是我有個家人及朋友的網路在支持我,所以我可度過失意那些日子。有人可能沒有這樣的網絡支持他,也沒有資源,或是完全不知道到哪找資源,所以他就像溜滑梯一樣,往社會下層滑落。林永頌在幫助這數百個卡奴過程當中,他後來也認為,還是要有完整的社會救助體系,不能只靠家人,因為家人也可能支撐不住。像我訪過一個家庭有個植物人需要照顧,然後某個家人又突然生病;或是生下特殊需要更多照顧的孩子,還有父母失智等等,社會總有不安全的一面,如果只靠親朋好友,沒有社會福利制度,真的會非常艱難。林永頌最後說了一句話:「社會要安定,就是要讓底層人能有尊嚴地活下去。」 這讓我想起東京大學畢業的第一線社會工作者,如今是東大教授的湯淺誠寫的《反貧困:逃出溜滑梯的社會》一書,在這本書裡,湯淺誠描述日本就是這樣一個溜滑梯的社會,他在書中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,一個五十二歲的男子,被發現時,已經死掉一個月了,屍體都變成木乃伊了。他在最後的日記裡寫著,好想吃一顆飯糰。在日本這麼富裕的社會,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?為什麼他不出來求救?原來這名男子因為肝硬化無法工作,後來社會救助又被中止,他又不造成別人的麻煩,死前家裏就剩下幾個硬幣。其實台灣也有這樣的故事,但是我們在媒體經常只看到結果,比如父母帶著孩子去自殺,或是誰已死亡,少有記者去追蹤死者生前經歷什麼事?這幾年我閱讀許多日本學者研究貧困的書籍,像NHK做過類似調查,追蹤孤獨死在家中的人,生前經歷過什麼事?那個紀錄的也是一個人向下滑落的過程。 我很難忘湯淺誠在書裡寫的一段話,「有人說,自己的人生要自己負責啊,但是這種『人生自己負責論』,就等於將沒有人依靠這件事合理化了,但是這些高呼人生要自己負責的人,應該也不是啃著自己一個人活過來的吧?」其實我們是靠著關係,網絡存活的,如果當一個人在墜落過程中,有任何一個人或制度伸手接住你,你也許就不會再往下滑了。 回到遊民,我後來訪問了一個在台北街頭流浪二十年的老馬,老馬很會畫圖,也很有論述能力。他說他常常自我檢討,到底自己為什麼會被社會淘汰?是當年沒有用功讀書,還是沒學好技術?像他是獨子,父母過世後,他也沒能力成家,就一個人想盡辦法照顧自己。剛開始他在染整廠工作,後來老闆因為產業西進,自己小工廠沒有競爭力就跑了。後來他拿出存款出來擺地攤,警察有每天開單。之後跟朋友合資開旅行社,錢又被朋友騙光了,就到台北火車站來。老馬說,在火車站經常被趕來趕去,以前還可以放東西,後來街友不在,東西就被清掉了,小馬非常生氣被這樣對待。老馬感觸地說,貧窮不是罪,社會要對抗的是貧窮,而不是遊民,他們很努力在生活,可是這社會就是一直打壓他們。 *勞動環境連動 街頭上越來越多年輕遊民 *老馬流浪二十年,對遊民的觀察是蠻令人怵目驚心的。以前他看到的遊民都是因為失業,才變成遊民;可是後來看到新一輩遊民是根本找不到工作。其實回頭看我們的外勞政策,兩千年外勞是32萬,到了2017年,是64萬,等於64萬的工作就是被外勞取代了,原本做這些工作的勞工,如果要再找工作,就要往上找比較需要專業知識的工作,才可能有機會,可是這群邊緣勞工又沒辦法符合這些需求,可能從此就再也找不到工作。老馬說的那些根本找不到工作的年輕遊民,可能就是這群人。我後來就在街頭經常遇到了他們。 對於外勞政策對台灣本地人的影響,我們太少去討論了。我常在我們社區看到許多有錢人,其實家裡根本沒有老人,卻可以請得到外勞,像我的鄰居,一對夫妻住了九十坪大房子,請了一個外勞照顧他們十幾年了;還有搭電梯時,經常看到外勞幫公主、小姐背書包,帶他們上學,我一直不解,我兩個寡母要申請外勞非常困難,為什麼這群人就是可以申請到外勞?可是這群有錢人,以他們的財力,如果請個外勞成本是三、四萬,他改請一個本地勞工,也許多付個一兩萬塊,但是改善的就是本地一個家庭。我們沒有好好檢討這個外勞政策帶來的社會後果,這個社會後果,造成一群人失業,往下沈淪,政府是否要規劃政策上去扶助這群人?而不是不斷地幫有錢人找群低廉的勞動力?回到為什麼我一認為個案非常重要,因為你會在這些個案的私人經驗裡,看到公共性,看到社會結構出了什麼問題?一個人的貧困,落難或沈淪,從來不在個人,而在社會。這是我認為報導個案非常重要,也是記者工作對台灣很重要的地方。 |
|